获释日本人质自述: 告诉你我看到的伊拉克

【2004/06/28 日经BP社报道】 4月7日,我在从约旦首都安曼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途中,被伊拉克费卢杰附近的圣战组织(伊斯兰圣战士)绑架了9天。我伊拉克的目的主要是救助街头的流浪儿,这是发生在我第四次准备到伊拉克时的事情。
我做志愿者的原则是不依靠NGO(非政府组织)、所以没有接受任何机构的资金援助。因此,每次回国时都要在千岁市的自己家附近打挤奶的零工来获得从事志愿者活动的费用。由于计划第四次到伊拉克时最短呆上2年、最长停留5年左右,因此,在今年2月回国时就已经决定,早晨去挤奶、晚上到酒吧打工。
不过回国后才发现出乎我本人预料的事情:1月份有关我的新闻报道见报后,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捐款已经汇到了我家。到4月1日我出国时,捐款数额已经达到了200万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5.4万元)。我的想法是:使用这笔巨款租借一些救助流浪儿童的设施,最终成立一个全部由伊拉克人组成的儿童救助机构。
计划还未开始就碰上了绑架。4月15日被释放后,我们才通过巴格达日本大使馆得知:我们是被作为让日本自卫队撤出伊拉克的人质,武装势力发表了有关声明,而且绑架事件在日本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到了迪拜之后,又从政府和家人那里听到了“自身责任论”和“自导自演”等说法。
我给日本外务省等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确实非常抱歉,同时我也感谢政府的救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从北海道到冲绳,在每一位曾经担心过我们安危的人、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感到愤怒的人面前跪下谢罪。同时告诉每一个人伊拉克的事情。我现在真的只想说对不起,我愿意向人们表示歉意。
由于一连串的刺激,现在我还无法一个人独自外出。呆在家里的这些日子里,我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虽然没有被那些拿着武器的伊拉克人活活烧死,但是我的心却被没有武器的日本给烧死了。
我现在,面对自己的这条残命,只有哭泣、发抖,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了。我甚至不能到伊拉克对那些为了我的自由而奔走的伊拉克人、接手我的工作在当地救助流浪儿童的伊拉克人说一声“谢谢”。
如果现在我要向公众介绍伊拉克的现状,或者说还要去伊拉克,肯定有人会说“这家伙又在胡说八道”,就如同自己会被吊在桥上示众一样感到可怕。
但是,就在我家对面的自卫队演练场上常常传来和我在巴格达听到的一样的声音,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我耳边仿佛又传来了在美军空袭下丧生的伊拉克人临终的惨叫、脚被炸飞时孩子的哭喊、弹片飞进体内时痛苦的叫喊,以及被美军虐待时的呻吟。
在被绑架时,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想来,觉得那仿佛是费卢杰的人们在抓住我的双肩、晃动着我的身体说:不光是用眼睛用耳朵,还用你的身体体验一下我们的痛苦吧!
我曾经答应为了人质的获释而费尽苦心的伊斯兰圣职者协会的长老,一定会告诉人们伊拉克的现状。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今后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是我想现在我可以一点点地讲出我在伊拉克的所见所闻。
因屈辱而报复的恶性循环
在今天的伊拉克,美军每天都在施加暴力,其结果是产生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对美军仇恨和厌恶的伊拉克人个人越来越多,最终走向报复美军,彼此间的相互仇恨不断增幅。
关于绑架事件,我最想说的就是:尽管2003年5月1日已经宣布战争结束,其实不过是从那一天起,当地居民和占领军队之间的战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伊拉克人、特别是费卢杰及其近郊拉马蒂的人们,这一年来一直过着困苦的生活。
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在伊拉克首都被联军攻克后的2003年4月29日。刚到巴格达,就听说美军在费卢杰枪击了要求和平的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我当时想的就是“太糟了!”,于是5月1日赶往费卢杰。费卢杰位于巴格达西边、车程约1小时。
首先在医院见到的是遭美军枪击的15岁和21岁的男子。看到那里恶劣的医疗条件,心想不找来医疗物资可不行。当时,170个床位只有1名医生。橡胶手套、注射器和氧气等都严重缺乏。发电机无法运转,保存保育器和医药品的冰箱也停止了工作。拉马蒂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为了呼吁各国NGO向费卢杰和拉马蒂输送医疗物资,我5月底回到安曼。6月初,带着前来救援的日本NGO成员以及几百万日元的医疗物资,我再次进入巴格达。
当时,费卢杰和拉马蒂的治安状况一直在恶化。由于萨达姆·侯赛因前总统属于逊尼派,因此美军对属于逊尼派势力范围的费卢杰和拉马蒂地区一直保持着超乎寻常的戒备、态度也非常粗鲁。这反而在当地群众的心中播下了反美的种子,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进入6月份,当地的普通民众也开始携带武器,甚至有人趁夜色在路上掩埋炸战车的地雷。
于是美军加强盘查、严格限制夜间外出,那一段时间经常可以听到美军在晚上误伤儿童的事情。天亮之后,会发现在长达200~300m的范围内都有弹痕。
拉马蒂的伊拉克人曾经告诉我这样的事情:被流弹击中、内脏受损的伊拉克人,虽然做了手术,但还是感到剧痛,于是乘车前往诊所。途中遭到盘查、被美军从车中拉出,受伤的伊拉克人用不流利的英语说出“医院”这个单词,美军的回答是:“回家等死吧!(Go home and die!)”。
跟我说这话的伊拉克人嘴唇颤抖着说:“从那时起我发誓要报仇!”。
搜查民宅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从深夜到清晨,美军常常突然破门而入。女性连服装都来不及穿就被赶到门外。一名伊拉克居民直截了当地说:“来家里搜查的美军摸了妻子除了丈夫谁都不能摸的地方,所以我开枪打死了四名美军”,让我感到震惊。
这种状况到2003年11月到达顶点,在2004年4月美军的讨伐作战中,更是有很多伊拉克人丧生。尽管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虐待事件被曝光,出现了解决的迹象,但是在此之外,伊拉克人体验了许多我们所无法得知的屈辱。
沉醉于稀料的孩子们
在费卢杰周边治安的不断恶化的同时,6月中旬我注意到在巴格达由于家人在空袭中丧生、或者从某些设施里跑出来的流浪儿童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是15~20岁的男孩子,住在巴勒斯坦宾馆附近的10层建筑物地下堆放垃圾的地方,多的时候20多人住在一起。
那儿被称为“喜来登”。在散发着恶臭的恶劣环境中,到处都是类似于稀料和酣乐欣(Halcion)那样的麻醉药品。孩子们靠行乞、给别人擦皮鞋赚来的钱又全部用于药品或吸毒了。
由于化学药品的影响,即使是互相之间的轻微碰撞,或者谁多拿了一棵生菜,伙伴之间就会马上争吵起来,用刀子或者破碎的可乐瓶斗殴的情况一天发生多次。自残行为也频繁发生。
伊拉克的成人对这些儿童放任自流,无人关心。侯赛因政权时,流浪儿童都被看作是国家的耻辱,只要发现就会被遣送到收容设施。由此,伊拉克的大人们都称这些儿童是“阿里巴巴(小偷)”,用冷漠的眼光看他们。有的大人甚至用脚踢那些由于吸入稀料过多而口吐白沫痉挛的孩子。
即使是把这些孩子们收容保护起来,他们也经常逃掉,所以各国NGO也不得不中途放弃,优先救助那些品行良好的孩子。结果,“喜拉登”那里就只剩下品行恶劣的孩子了。我想我不能丢下这些孩子,因为我上中学时也吸过稀料,知道他们在和大人打交道时的无助处境。
去年11月,在我第三次到伊拉克时,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自立的环境,在“喜拉登”附近以每月175美元的价钱租了一栋公寓。在伊斯兰,女性一个人生活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每天从旅馆赶到公寓,每次叫来一两个孩子,给他们洗澡,换上新衣服并提供食物。对随意扔掉肥皂或面包、或者卖掉我送的毛毯等不珍惜东西的孩子,我会很生气,会大声地训斥他们。
渐渐地,本来对我很苛刻的伊拉克大人们也开始来帮忙。每天都有人来公寓,帮我翻译、洗衣、打扫卫生,以及帮孩子们洗澡等。某建筑公司老板斯莱曼(Souleymane,音译)还送来了一些钱,并说:“现在正是建筑高峰期,工作忙,不能帮你做什么,这些钱你拿去,给孩子们买一些食物和衣服”,甚至还为孩子们的就职而奔波。这些帮助真的让我喜出望外。
但是,公寓的房东开始变得越来越贪心,开始让我交两倍的房租。钱也快用完了,结果只好退房。今年2月为了凑够1~2年的房租,我再次返回日本打工。前面已经说过,由于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捐款,2个月之后我就出发到伊拉克去,结果在中途遭到了绑架。
绑架带给我的教训是,匆忙行事难以获得好结果。现在想来当时一定是太担心留在伊拉克的孩子们了,所以心情有些焦躁。当时伊拉克的朋友在邮件和电话里跟我说:“孩子们每天都在期待,经常问‘菜穗子什么时候回来’”。
无法选择死亡方式
但是去伊拉克时并没有放松警惕。我知道因为日本派遣自卫队,伊拉克人开始出现反日情绪,于是我在安曼伊拉克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汽车站、食堂等地方搜集了一下信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才去了伊拉克。
对于自己的行动我一直是打算自己负责的。虽然现在我还在考虑什么叫做“自身责任”,但直到绑架发生为止,我都是做好了遇到危险的准备了的。我想所有去伊拉克的人都做过最坏的打算。绑架事件发生前我自己也知道:可能会在劝解流浪儿童时被刀子刺中、被卷进爆炸恐怖事件,或者被美军的流弹击中。
我当然不想死。但是,在众多的危险当中,我无法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去伊拉克或者出远门时,这些事情在脑子里闪过,那一瞬间曾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类似“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的话。
不过,尽管自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过刚被绑架时的确非常害怕,拼命乞求绑架者放一条生路。过去在伊拉克时我没有钱请不起翻译,所以逼迫自己记住了许多阿拉伯语的单词,能听懂一部分会话。曾经对日本有非常好印象的费卢杰的人们会我怒目而视说,“日本人很坏,去死吧”。
被绑架期间,大都是我用英语和伊拉克人对话,所以他们说,“这家伙会说英语,肯定是间谍”的话我都听懂了。比如大家看到过的录像中的镜头--当他们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想这次真的是要死了,当时并不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刀背。他们绑在自己身上的手榴弹会不会突然爆炸了?当时想到了很多意外,越想越害怕,所以一直都在哭泣。
从绑架的第三天到被释放为止,圣战组织在其头目的指示下,我们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伙食也有很大改善,可能被杀这种危机感才少了许多。从那个时候起,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对话的重要性。
到了最后,一直有一个懂英语的人跟着我,我跟他说:“绑架是最坏的解决方法。日本人会觉得伊拉克人危险而且可怕”。他回答说:“我也明白,不过除了使用武器,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法。我们只能这么做”。我想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就一股脑地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那时我还谈到拉马蒂的一个翻译卡斯木(Qasim,音译)的事情。卡斯木起初也憎恨美军及其盟军,尽管没有参加攻击美军的行动,不过对攻击行动持赞成态度。长老们也是一样。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的观点,开始考虑和平解决的方法。
我说过这些后,这个懂英文的人说:“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怎样才能和你成为朋友呢”,他这样跟我说了两遍,眼里含着热泪。
因为绑架者没有归还我们的贵重物品,所以我很生气地说:“你们自称是什么圣战战士,结果和阿里巴巴有什么区别。我真想杀了你们”。我这样做是想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一来他们反而态度变好了:“和平!和平!”,“把丢失的东西列个清单给我。相机等物品可能找不回来了,现金的话可以想办法凑齐”。
我说:“我们的钱都是为伊拉克筹集的。如果你们能够筹集到钱的话,就拿这些买些药品什么的”。同时我还强调说:“就是不能买武器!”。我被释放时,圣战组织的一个看似领导的人送给我一大瓶纯蜂蜜表示歉意,说是送给日本的礼物。遗憾的是蜂蜜最终被忘在了巴格达的日本大使馆。
伊拉克传来的好消息
知道将被释放的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释放后记者来采访,我说:“我还是无法讨厌伊拉克人”。当我通过大使馆的电视看到小泉纯一郎首相对我说的话发表讲话“真希望她有点自觉性”后,开始精神沮丧。如果我当时说“讨厌”的话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在大使馆,驻伊拉克大使大木(正充)说:“自卫队没有撤回的理由。刚刚派出来就撤回去,面子上也过不去”,这番话令我非常震惊。我也明白既然人质已经获释,当然没有必要撤回自卫队,但是听到“面子”这样的话,我心里很难过:“完全没有考虑伊拉克人以及自卫队队员”。
日本警察厅外事科一位叫吉村(Yoshimura,音译)的先生也来调查事情的经过,连名片都不给,只是对我说:“调查的内容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可是那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却被作为NHK新闻在全国播放。在调查的最后,他说:“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向任何人谈起。因为我也有家庭”。
那时我没有说任何话,不过心想:“伊拉克人也都有家庭啊。不正是因为他们的家人被杀害了,事情才变成这样的?”。这两次经历让我非常难过。紧接着就是我回到日本后,回答有关自身责任论以及自编自演的质询。在我感到很抱歉的同时,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
不过,从伊拉克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就是最近的一天早上,我接到了援助流浪儿童的斯莱曼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们收到了1000多封给菜穗子的信。而且我已经决定按照菜穗子的意愿,开办儿童援助设施。设施的名称就定为菜穗子”。
听到这些,我想说“不必这样”,可是话没出口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住在拉马蒂的朋友卡斯木那里也传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他在邮件中这样写道:“我们正在一边协助美军,一边推进和平建设。菜穗子被绑架后,一定要按照菜穗子说的去做这种想法愈发强烈,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修复在空袭中被毁坏的两所学校”。
真是太了不起了,真的。曾经对美军主导的国家重建是那么愤怒的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了。
我没有读过日本宪法,但我认为其中的第九条“通过对话解决纷争”,实际上说的就是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这不仅是NGO和政府官员能够做到的事,我们每个普通人和你的近邻、和孩子们、和外国人谈论和平也是实现和平的一种方式。
身体状况刚有好转,就又从伊拉克传来了两名日本人遇难的噩耗。愿他们早日安息!。我不希望任何生命受到伤害,谁能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让人们有放下武器的勇气呢?
高远菜穗子:1970年1月生于北海道千岁市,现年34岁。1992年毕业于日本丽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在东京工作一年后远渡美国发展,回国后在日语教师教育学校进修。为了学习经济方面的知识,从1994年开始直到30岁经营卡拉OK店铺,2000年开始在印度、泰国和柬埔寨从事志愿者活动。2003年到伊拉克,凭借个人的力量向伊拉克提供医疗设施以及救助流落在街头的流浪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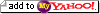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 Home